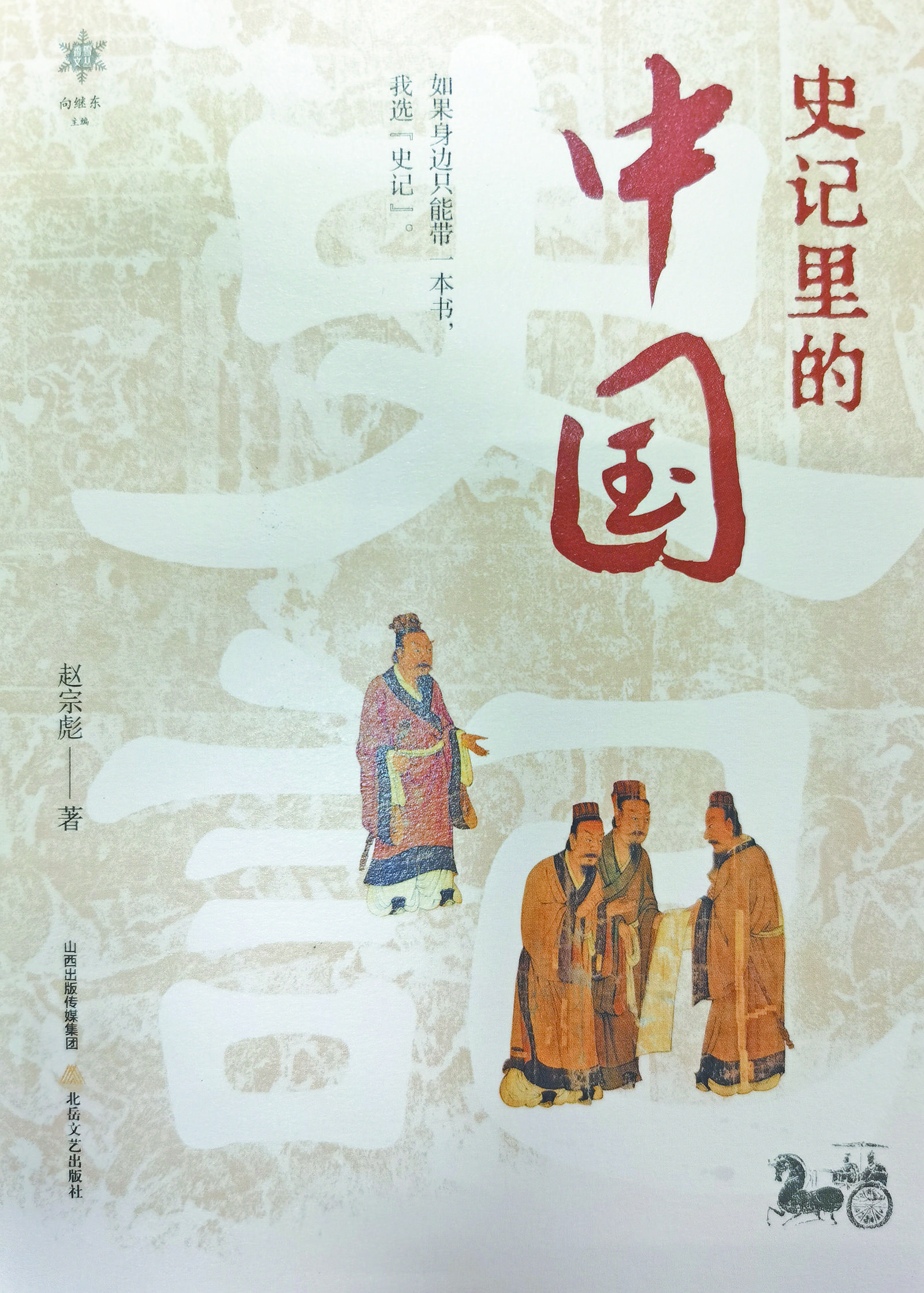
读赵宗彪先生新著《史记里的中国》,感到其中折射出来强烈的现实关怀,心头是激奋的。
司马迁一定想不到两千年后,他的文字还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于太史公无疑乃莫大安慰,于后人则难免悲喜交集。
人是容易淡忘的动物,非不得已,很少有人刻意去翻老皇历,只有遭逢某种境遇,如文艺复兴于中世纪末的欧洲,社会发展面临严重困扰与无可规避的选择,有识之士才会去过往岁月中着力寻找参照与启示。
不由得想起上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至今仍觉经典。提出这个论断后,老人家作过如此解说:“惟有当前活生生的兴趣才能推动我们去寻求对于过去事实的知识;因此那种过去的事实,就其是被当前兴趣所引发出来的而言,就是在响应着一种对当前的兴趣,而非对过去的兴趣。”
这里的“兴趣”,我以为至少还含了关注与责任的意思在内。因此用这话来形容或解释司马迁的史记创作,也是合适的。
而赵宗彪读史记,无疑亦带着相近的情怀。
此书目录编写,在每篇文章的标题下面,均用几句话来表达作者从史实中总结出的史识。他是司马迁,也是克罗齐的知音。不妨抄录几段:
“世界上明白人不多。
为什么不多?因为人性如此,人总是自以为是,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低估他人的水平。”——《做明白人很难》
“君主们当然知道大部分臣下没有谋反之心,但是,只要臣下有了一定的能力,无论他如何表示效忠,对君王而言,最好的效忠,还是到黄泉最彻底。明朝的朱元璋一当上皇帝,立马杀胡惟庸、杀蓝玉,也是一种制度的惯性使然。”——《功臣可以不死吗》
“当沧浪之水清澈时,濯缨。浑浊,还行,可濯足。但是,当沧浪之水变成了泥浆或全部干涸,仅有一个沧浪之名了,你如果还想濯缨、濯足,不就是自赴泥沼以求死吗?”——《假如沧浪之水干涸》
“羊斟的战争,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一个‘人’的战争,是为了捍卫自己尊严的战争,也是小人物对抗特权的战争。既然华元可以倚仗自己的职权不给羊斟羊肉吃,羊斟同样也可以凭借自己开车的职权让耀武扬威的司令官当一回阶下囚,这不是很公平吗?”——《个人的战争》
“世界上,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付出实惠,获得恩情;付出仇恨,收获报复。将这一铁律证诸古今,概莫能外。而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将会失去所有的朋友,留下的,只是敌人。信用的价值,也就是人的价值。”——《信用的价值》
书中赵先生屡次讲到,他觉得司马迁有种远超那段历史的现代意识,这当然不可能,令他产生错觉的,一定是当下与历史发生了相当程度的重叠或者说归返。
直到看了后记,才知道本书并非新作,分别写于2014年(前28篇)和2003年(后10篇),两者相差达十年以上。
我无疑更喜欢前面那些后写的篇章,对后面那些先写的部分,则较少感触。
这可以看作是作者个人史学上的进步与史识的成熟,仔细想来并不止于此,而是此间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惟有身历其中,才可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从前与现在的中国。当然,这得有敏锐的知觉与感触。赵宗彪无疑具备这种能力。
所以有某种先见之明的,应当是作者本人。无论如何,能在十年前写出令人觉得强烈关照当下的文字,实属难得。